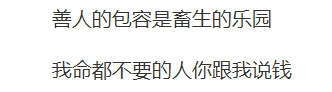
#每月应许电影
这个月我想看“石榴的颜色”,我忘了是在哪篇影评还是什么里面看到的,推荐说是意识流大作,评论里也是清一色的“好美,像诗”感觉好有意思。
上个月本来说重看最后一个男人但是没看😩也不知道干啥了但是把好久之前推过一次两杆大烟枪看了,很有意思!连环计那里笑死我勒,配乐也都好好听。还看了昆丁的落水狗,也推推这部!转场方式很牛!还有经典名言“对不起,我是警察。”(各大网站上的好像是删减版的我找资源看的)
#碎片饮酒
这几天去朋友家玩了,因为说好请大家喝酒,就带了很多果汁买了伏特加给大家调了很多鸡尾酒,都是之前分享过的就不再重复了~
因为大家都很感兴趣所以调了可乐桶,冰块装满然后挤了一个柠檬,怕味道不够还加了淹没一两块冰块的柠檬汁,我们直接用水壶喝的(...)所以把200ml的威士忌小瓶直接倒光了然后倒了大概800ml可乐,喝起来比较像柠檬可乐但是喝下去还是能喝到酒味~上头倒是没有大家喝的都很开心(变喝边打牌本赌王又赢钱了嘻嘻)
今天餐酒选了维斯特玛白葡萄酒,700ml只要五十块!虽然不及沃尔玛那个便宜但味道不涩很醇很润还有点葡萄酸酸的味道~我很喜欢~
晚上跟我爸一起吃饭,好像好久都没有跟他一起吃饭了。吃完饭我们一起走回家,他突然跟我说:明年你也要工作了,我再熬个五六年把自己的事情搞完,就可以了。
我一直没给我爸说我要考研的事,关键原因在于上一次提起得到的结果不怎么样,我想的就是考了再说,考上想办法读考不上不说当没发生,于是就没有在这个档口给我爸讲,只听他说接下来的安排。他说:你以后自己工作了也不用找我要生活费了,你想办法把自己顾好以后别来找我,我也不去麻烦你就行。
然后他谈自己的打算:先存两年钱把养老保险补了,再存点闲钱,等客车驾照到期再去买个几万块的二手面包车之类的车,把后面改装一下放个床垫拿点做饭的东西,然后就出发。
我听了之后问他:没事就出去玩玩?我爸不屑:找时间?到时候直接天南地北地跑几年,一个人沿国道开开心心地走几年。
他说:我一辈子,累了一辈子,憋屈了一辈子,至少也想最后这十几年什么也不用管,为了自己开心快了地活一段时间。
我衷心地祝愿这一切都顺利。
我今年21岁了!(今天不是我生日)我21年都没冲动过,出去玩会提前做安排,吃饭会美团看评论,离家去网吧都会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唯一跳脱的事是醒了不想去上课逃课,而这样的我,今天,终于疯狂了一次。
时间推移到五点多钟,我的两个朋友突然给下午才起床正在吃饭的我发消息说过来找我吃饭,我想了半天说五六天没出门了,干脆出去玩玩嘛!就答应了然后止住了吃饭的动作,洗了个头,跟他们去吃饭了。
到了吃饭的地点我才知道他们最开始其实没有想过来找我!!(跨区)是闹着玩的,但是我都答应了就还是来了。
时间再过去一个小时,大约七点半八点半,吃饱喝足的我们聊着消食去到了旁边的水族馆,结果因为不太满意水族馆1.闭馆了,2.馆太小了而坐在了大门口纯聊天,聊着聊着就突然聊到成都的那个水族馆比我们这个要大一点好一点。
总而言之,在我们聊到这个话题的十分钟后,我们已经买好了去成都的票,同行三个人里有两个身份证都没带,每个人身上只有一两百块,却已经坐在了去高铁站的车上。
一切都发生的迅速至极而又不真实,我复盘的时候跟朋友聊起,想要是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有误我们现在都不会在这辆列车上,妈呀,我们决定的十几分钟里甚至包括了买票和打车以及考虑没有身份证怎么办!像一场突然落下的急雨,把已经坐到高铁里的我都打的措手不及。
我21年从来没这么疯过!哪怕好像也不是很疯,但是给予我的快乐和刺激都是这21年来没得到的,太神奇了,我的手甚至都在抖,我突然突然好快乐好快乐 
#碎片饮酒
又政治性抑郁了,烦了一天,晚上跟室友出去吃饭,刚好学校旁边开了罗森,买到了食用冰回来麻木自己了。
这次调的是完全不正宗大都会和金酒螺丝钻,大都会的原本调料是:伏特加+君度+蔓越莓汁+柠檬汁,我没有柠檬汁和蔓越莓汁,独创版本是伏特加+君度+树莓车厘子混合汁,丢了几颗樱桃进去,还专门帮室友削了一个橙子搞到点橙皮抹了点汁。因为我的伏特加不多了这次直接倒完了,喝起来觉得全是果汁味大饮几口上厕所的时候感觉血气汹涌,鸡尾酒的阴谋!
螺丝钻是金酒+橙汁,“新的橙汁”一级棒,它们的浓缩果汁兑水兑酒都很好喝~ 螺丝钻还可以兑伏特加,我一般是喝伏特加般的但是上述没有了所以换了金酒,味道也很不错!为了消愁放酒放的很多🤤
#碎片饮酒
在食堂白嫖了一杯冰!很兴奋的回寝室喝酒了。
这次看了半天酒单,最后自己把朗姆,伏特加和君特力娇混在一起了!加了柠檬和苏打水。
可惜这次的柠檬没啥味道,给我喝的很不爽,最后室友给我援助了一罐mini雪碧,于是我瞬间拥有了三杯酒()雪碧的味道很大,但是因为混了三种酒劲很大....我这个上脸怪立马脸红了。
学会了无开瓶器开玻璃瓶饮品和用携带杯摇酒,嘎嘎。
#墙国观察
转自微信公众号@烟酒小僧:
《寻找尸体的人》报道被删除风波
4月7日,搜狐新闻极昼工作室刊发了《寻找尸体的人》。
作者希望能不删稿子,但还是被删了
第二天,一个微信群里传出消息:文章的第二作者小陈是一名在读大学生,他的父母正在被汕尾当地警方骚扰,“并要挟他今晚返乡报到。”
小陈帮助了文章第一作者翻译当地方言,目前,派出所的人还在他的家中。有人尝试联系小陈,但是联系不上。
当地派出所晚上10点左右已经离开他家里了,学生一直在学校里,是学新闻的。
根据《寻找尸体的人》报道,2021年1月初,一份判决书揭开了一段颇为骇人的往事:
2017年2月,陆丰市湖东镇人老黄到了肺癌晚期,病榻上,他向弟弟黄庆柏表达了自己的遗愿:不想火葬。
早在2012年,陆丰所属的汕尾市推行全市火葬“一刀切”,禁止土葬,禁止出售棺木。
黄庆柏出资10万7千元,通过多重关系,找到了在当地替人运载灵柩的瘸腿司机陈丰斌。中间人找到陈丰斌,告诉他,需要一具可以用来顶替的尸体。
2017年3月1日,陈丰斌开着面包车,见到路边拾废品的36岁林姓智障男子,朝他招了招手,然后将他推上车,灌酒。陈丰斌后来在口供中交待,“他喝酒喝到吐,我又继续给他喝,他喝到不醒人事了。”似乎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他说,“我自己也喝了一杯。”
等到智障男子没反应了,陈丰斌觉得他大概已经喝死了,用四颗钉子封进了事先准备好的棺木,藏在家附近,又遮上些树叶掩盖,然后给中间人打电话,说现在有尸体了。
2017年3月3日,老黄出殡。两幅棺木被调换,智障男子被运往殡仪馆火化,而老黄的棺木被埋在事先选定好的墓穴,就在水库边,黄家请一位外省的风水先生看过,坐山望水,主富,寓意“望财”。
林家人一直不知道智障男子的去向。直到两年半后,2019年11月,镇上派出所打来电话,才知道智障男子已经死了。
2020年12月,陈丰斌案二审开庭,法院认为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案件中的另一些涉事人员,例如中间人老温,在事发后不久,因突发疾病去世。另一个中间人,原殡改工作人员梁成龙,在2020年4月被陆丰市人民检察院认定不符合起诉条件。买家黄庆柏,判决书中同样写道,“已被不诉”。
https://mp.weixin.qq.com/s/kGNFSPe8jxX0waqO_LjSxQ
《寻找尸体的人》
转自极昼工作室
摘要:2021年1月初,一份判决书揭开了一段颇为骇人的往事。广东汕尾陆丰市一位因病去世的男人不愿火葬,而早在2012年,汕尾市推行火葬一刀切政策,要求全市火化率达到100%。家人为了保留其完整尸身下葬,出资10.7万元寻找一具能顶替火葬的尸体。一个瘸腿的男人为此杀害了路边偶然遇见的傻子。
文丨李晓芳 陈锴跃
编辑丨王珊
视频剪辑丨汤赛坤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083020?event_source=timeline&source=timeline&dt_dapp=1
失踪的傻子
村里的人都知道,林家那个傻儿子失踪了。具体是死是活,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没人知道。林家为此报了警,全员出动找了好几个月,没有任何结果。
失踪的第二天,村口小超市老板特意去问林家兄弟,“你们家那个呢?”傻儿子性情温和,脑袋虽然不灵光,却喜欢往人堆里凑。他常和整个村乃至隔壁村的傻子赖在村口小超市门前,最热闹的时候,能有三四个傻子蹲成一排,眼睛斜斜瞟着,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林家设想过各种最坏的结果,“想过我二哥会不会走夜路,不小心掉进池塘了。“家里最小的儿子,28岁的林再龙说。乡间有流言,一些看起来无依无靠的老人、流浪汉,会被抓走卖掉器官。林再龙听了,总忧心自己的傻二哥也遭遇了这种不幸之事。
林家的傻儿子出生于1981年,家里六个兄弟,他排行第二。六个月大,母亲陈香妹发觉这个孩子有点不一样,表情呆呆的。长到该开口说话的年纪,他一句不会说,大人的话也听不懂。陈香妹心里大致有了判断,这孩子可能智力有缺陷,是傻的。
陈香妹想,傻就傻吧,只要他学会饿了说吃饭就好。儿子顺利长到30来岁,一张肉肉的圆脸,小眼睛,不到1米6的个头,身体壮实,几乎不怎么生病。她从小手把手地教,尽管他还是“讲话含含糊糊的”,外人听不大懂,但能表达吃饭、洗澡、睡觉等简单的日常需求,能自理生活,记得住自己的名字、住址。陈香妹很满意了。
如今她68岁,眼白浑浊,像蒙了一层雾。提起艰难养大的傻儿子,眼泪总也止不住,“一想到他,我的心就跟被刀绞一样。”
失踪当天,傻儿子接近中午才起床,吃过午饭就说要出门捡塑料瓶,换钱买烟、买好吃的。他一辈子都生活在广东省陆丰市金厢镇,熟悉镇上几个村子的道路,每天都会出门转转,捡拾废品、看戏,到了晚上准时回家,从没出过意外。
傻儿子戴上荒漠迷彩军帽,出门后,先去了弟弟林再龙家。那年,林再龙刚结婚,有了孩子。他喜欢白白嫩嫩的小侄子,时常过去看一眼,逗一逗噗噗吐口水的小婴儿,跟着乐呵呵地笑。坐了一会,他拎起蛇皮编织袋,说自己要去捡瓶子了。那是他留给弟弟的最后记忆。
傍晚六点了,陈香妹有点心慌,傻儿子还没有回家。平常饭点到了,他一般早到家了。她喊小儿子林再龙,“你哥从一点钟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林再龙安慰她,晚点就会回来了。
母亲似乎总能率先察觉到某些不详的开端。当晚,陈香妹睡不着,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深夜12点,门口依旧没有传来熟悉的、像含着一口糖喊妈妈的黏糊声音,陈香妹爬起来给三儿子打电话。三儿子在广东乌坎打工,接了电话连夜开车赶回陆丰。天一亮,一家人出门找人,把金厢镇上的几个村都翻了遍,但一个活生生的成年男子就像汇入大海的雨滴,全无踪迹。
林家的傻儿子失踪于2017年3月,一直到两年半后,2019年11月,林家接到镇上派出所打来的电话,才得知他在失踪当日已经死亡。今年1月初,一份刑事裁定书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描述了事发当天的全过程——
离开林再龙的租屋后,林家的傻儿子又走了两三百米,拐到村里的大路上,那是一条繁华、车流不断的村道,路边有两个公共垃圾箱,林家的傻儿子正弯腰从垃圾箱里掏塑料瓶,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他身边,车上下来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和他交谈几句,判断出他有明显智力问题,将他半推半拉上车,驶离了金厢镇。
路上,中年男人买了六瓶30多度的红米酒,全数灌给了林家的傻儿子,然后将他装进一具事先准备好的棺木,用钉子封住,杀害。
杀人的原因听着有些荒诞:当地一名50来岁,因病去世的男人不希望被火化,要求土葬。有人出钱,就有人愿意打包票帮他办好所有事情。林家傻儿子成了那个替代品,被杀害后当作替身送进了殡仪馆的火化炉。
找尸体的瘸子
开面包车的中年人陈丰斌和林家的傻儿子一样,都身有残疾。
陈丰斌外号“满地踩”,这是一句陆丰方言,指一个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陈丰斌从小辍学,少年时,就常在村里闲晃,和社会青年们称兄道弟,弟媳说,能来钱的事,他大都愿意干。
几位邻居却认为他“人很好”,“平时挺有礼貌的,和邻居们关系都很好。”邻居们说,他以前从未干过任何出格的事。
结婚后,陈丰斌的确安稳了一段日子,在村里承包了十多亩田地,和妻子黄英莲一起种青菜、黄豆,收成了挑去市场叫卖。侍弄土地全看天意,岭南潮湿,常常一场大雨下来,颗粒无收。但黄英莲说,那时她要买肉,或是给家里添置生活用品,能直接从卖菜钱里取现金,也算是丈夫给的家用。
2013年,就在卖菜的路上,陈丰斌出了车祸,整条小腿被直接碾过。他在床上躺了一年多,拆掉夹板后,伤腿也永远落下了后遗症,成了瘸子。他没法再干重体力活,田地全退了回去。村里没人说得清,不种地后,陈丰斌具体都在干些什么工作。但情况确实是在那之后开始出现变化的。
没了固定职业的束缚,陈丰斌越来越不着家,常常是隔好几天,带一身酒气回家。起初,黄英莲也会打电话询问他的去处,陈丰斌对她大吼,“我在玩女人啊,怎么样?”
回忆起来,黄英莲觉得有些尴尬,勉强勾出一点笑容,摊手,“他都这样说了,我还能去管他吗?”黄英莲也不希望他回家,每次陈丰斌回家,两人总会因各种家庭琐事争吵。陈丰斌会动手打她,有时是一记耳光,有时是突然踹过来的一脚。
黄英莲说自己并不了解丈夫,他在哪里,做什么,她全不知情。警察上门那天,陈丰斌难得在家,骑着摩托车接刚放学的儿子。几个亲戚,包括黄英莲都目睹了警车开过巷子,但所有人都语焉不详。他成了整个家族耻于提及的存在。
从他被捕、判刑到入狱,黄英莲一直没去看过,“我跟他感情不怎么好。我从来没有去想他,也没有去管他。”她觉得丈夫不回来,家里反而轻松多了。她的精力全在打工挣钱上,找了一份餐馆杂工的工作,加上亲戚时不时地接济,一人勉强负担了两个孩子和自己的生活费。她的背总是微微弓着,有种疲倦感,又有点像弯腰认命了。
根据2021年1月初公布的刑事裁定书,陈丰斌在车祸之后从事的工作包括替人运载灵柩。他认识了一位姓温的大哥,老温常常帮殡仪馆干活,开车运尸体,或送人到殡仪馆。忙不过来时,老温会让陈丰斌帮忙,运一趟灵柩的费用是200元。
关系是一点点搭上的。2017年2月,陆丰市湖东镇人老黄到了肺癌晚期,病榻上,他向弟弟黄庆柏表达了自己的遗愿:不想火葬。早在2012年,陆丰所属的汕尾市推行全市火葬“一刀切”,禁止土葬,禁止出售棺木。黄庆柏问自己的一位朋友,有没有办法实现亲人土葬的遗愿?朋友给了他一位殡仪馆工作人员的电话。
黄庆柏联系上殡仪馆工作人员梁成龙,时年58岁的梁成龙是原湖东镇党政办公室副主任兼殡改登记员。在后来的供述中,梁成龙声称,对方想要殡仪馆司机的电话,因此,他将老温的联系方式给了黄庆柏,他并不知道黄家调包尸体逃避火化的事情。但陆丰市公安局在移送审查起诉认定中写道:梁成龙与老温商定尸体调包事宜,并要求事成后其应分得人民币1万元。
老温接下任务,成了链条中的一名掮客。他和黄庆柏商量好,10万7千元,帮老黄实现土葬的遗愿。
价格谈妥后,老温找到陈丰斌,告诉他,需要一具可以用来顶替的尸体。
2017年3月1日,陈丰斌开着面包车,见到路边拾废品的林家傻儿子,朝他招了招手,然后将他推上车,灌酒。陈丰斌后来在口供中交待,“他喝酒喝到吐,我又继续给他喝,他喝到不醒人事了。”似乎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他说,“我自己也喝了一杯。”
傻儿子没反应了,陈丰斌觉得他大概已经喝死了,用四颗钉子封进了事先准备好的棺木,藏在家附近,又遮上些树叶掩盖。
他给老温打电话,说现在有尸体了。
3月3日是老黄的出殡日。到达黄家约定的地点后,一个抬棺人注意到,路口拐弯处还停着一辆白米黄色面包车,旁边也放着一副棕色棺木。离开时,他看到有人把那副棺木抬上原来推老黄棺材的四轮手推车上。
两方人马在这里将棺木调换,林家傻儿子被运往殡仪馆火化,而老黄的棺木被埋在事先选定好的墓穴,就在水库边,黄家请一位外省的风水先生看过,坐山望水,主富,寓意“望财”。
富人街的买家
陆丰村镇许多房屋因日晒雨淋又缺乏维护,一点不留情地显出岁月锈蚀的痕迹。但每个村的祖祠和伯公庙(土地庙)却是最崭新豪华的,外墙看不到一点青苔痕迹,香炉满满当当,香灰几乎要溢出来,香案却被擦拭得能照见人影。
这里的老人少则要供奉二三十位各路神仙,多则四五十位不等。有的杂货铺索性用货架一分为二,一半店铺卖香油、大米、鸡蛋,另一半卖纸钱、香烛、拜神金纸,对陆丰人来说,这些物件和粮油一样,都是日常用品。
陆金的店正对马路,他不到30岁,已经在这行待了近十年。店里专营红白喜事用品租赁,大到红白喜事宴客必备的桌椅杯碟,小到葬礼上不同亲属佩戴的不同尺寸的孝布,都能在这里一一备妥。店门正对马路,马路对面是一幅巨大的悬赏通告,写着一位姓陈的逃犯涉黑、涉毒,悬赏金额10万元。
陆金19岁时从父亲手上接下这项事业,经手的婚礼和葬礼,早已数不清。他在葬礼上听过许多老人的遗愿,要“全须全尾地进行土葬”,他们深信死后火化是粉身碎骨,不能庇护后代子孙,不能顺利转世。
广东省在1998年推行城乡殡葬改革,但汕尾市向来执行不严。陆金接班那年,正是2012年,全国严格执行火葬。汕尾市委、市政府也出台了一份全面推进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到汕尾殡葬目标管理考核,从2001年至2010年连续10年位于全省倒数第一名。而周边的其他地区,包括潮州、汕头等市的火化率已基本达到100%。
那年夏天,汕尾市推行火葬一刀切政策,要求将全市火化率提高到100%,每月对各镇、场区的火化率进行排名通报,考评结果和当地官员的晋升、评选挂钩。
几乎没人温顺地接受这项政策。许多人选择偷埋私葬。家族里兄弟多,人狠又能打架的会直接忽视火葬政策。曾有一位殡改大队的副队长和队员,在出殡当日前去阻拦,不仅被打,还遭到家属囚禁,公安机关到场后,才得到解救。
为逃避火化调包尸体也不罕见。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至少有四起相关案例都发生在陆丰。
有人试过用猪、羊等动物尸体替代,用别人的尸体替代,那更是有的。
2014年陆丰某村居民曾实名举报,为了完成奶奶土葬的遗愿,他找到镇上的殡葬改革负责人,询问能否像其他人一样,一切按火葬的仪式进行,然后在送往殡仪馆的路上偷梁换柱,将亲人遗体送回土葬。村民表示,“镇上的死者家境好些的都这样操作。”然而殡改负责人要价6万元,“我们家太穷,一下拿不出6万元,只好违背老人家的遗愿。”村民最后愤怒质问,“为何有钱和有势的人家可以出钱买名额搞特殊进行土葬?”
陆金的不少同行都干过帮人寻找尸体代替火葬的活计。他们的职业囊括红白喜事用品租赁店老板、丧葬乐队乐手、法师等等。特殊的身份让他们经常出入葬礼现场,对各村的死亡情况了如指掌——没有人能比他们更胜任这份工作。
适合调包的尸体并不好找,为了避免被人识破,有些买家会要求两具尸体性别相同,死亡时间不能相差太远,这样就算遇上殡改工作人员调查,也容易糊弄过去。一位红白喜事用品店老板曾帮买家找到一具死亡多时,完全白骨化的无名尸体,殡仪馆工作人员抬棺上火化台时发现重量偏轻,不像一个正常男人死亡的重量,让家属确认死者信息。家属异样的回避状态让工作人员起疑,最终上报到殡葬监察大队。
陆金听说过一位“厉害同行”,“承包”了当地存放无人认领尸体的冷藏库。一有订单,同行就能拉出一具符合要求的尸体进行调包替换。这些尸体多是流浪汉、乞丐、独居老人,“一般都找不到家属,被发现了也没有人找你麻烦。”
弱势、贫穷的人群是链条上任人宰割的一环。不止一位寻尸人接到任务后,明确寻找来自“五保户”和“穷人家”的尸体。一户五保户家庭有一位82岁的老人死亡,他们以3.2万元的价格将尸体卖给了寻尸人。另一户五保户家庭要价8万元,寻尸人嫌弃太贵,转向另一个提供尸源的人,最终以5万元价格购买了一具无名女尸,再转手以8万元的价格提供给买家。
这样的寻尸途径相对安全,被抓获只会判以盗窃、侮辱尸体罪,一方自愿提供尸体的行为也能成为庭上辩护轻判的理由。
但陈丰斌与这些寻尸人都不同,他直接选择杀害一位偶然碰到的智障男性。两年后,警方根据沿路的监控视频线索,将他逮捕。2020年12月,陈丰斌案二审开庭,法院认为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案件中的另一些涉事人员,中间人老温在事发后不久,因突发疾病去世。另一个中间人,原殡改工作人员梁成龙,在2020年4月被陆丰市人民检察院认定不符合起诉条件。买家黄庆柏,判决书中同样写道,“已被不诉”。
几起判决中,买家都是隐形的存在,没有人被追究责任。
黄庆柏兄弟的祖屋坐落在村里的“富人街”上,周围的邻居说,过去街上住的都是村里的有钱人,尽管富人们大多搬走了,但大家还是习惯性地称呼这条街道为富人街。如今富人街上看不出太多富贵景象,房屋多是年代久远的破旧小楼房,有居民辟了一楼门面做商店,卖当地的海鲜干货和廉价小商品。
但这条灰扑扑的街道上,黄家的房屋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存在。四层小楼在一众低矮民居里鹤立鸡群,几年前刚翻新过,外围的瓷砖、栏杆一尘不染。邻居们不愿多谈黄家,大家只说他们长年在深圳做生意,不住在村里。
村口用金色边框裱好的“芳名榜”还留有黄家兄弟的痕迹。上榜的都是给村里捐资修路、修亭子的善人,一排排名字用金粉镌刻在黑色大理石上。大多数人捐个一两千,而已经去世的老黄捐了一万三千元,给村里修建道路、积功德。
回不来的林少仁
林家花了大半年时间寻找傻儿子。“陆丰翻遍了,又找到深圳啊,广州。”弟弟林再龙说,当时他们几兄弟都停下了工作,只专注于找人这一件事。
60多岁的老父亲也跟着四处奔波。林家父亲的身体早就出了问题,之前被检查出严重的胆结石,儿子失踪后,林再龙说父亲的病更严重了,“他就一直痛一直忍着,实在受不了了才吃颗止痛药。也不去医院检查,一门心思就是要找儿子。”
林再龙记得,2017年6月底,有人打电话说在广州见到一个智障男子,长得很像林家要找的儿子。父亲当天就买了去广州的车票,结果自然是失望的。也是在那一次,父亲实在痛得受不了了,去了广州的医院做检查,被告知已经是胆囊癌晚期。郁郁寡欢地从广州回来,熬了十几天,父亲去世了。
“后来确实没办法。”林再龙的声音低了下去。每个兄弟都有自己的家,停工几个月,生活都快成了问题。他们向亲戚借了些钱,但也维持不了太久。兄弟几人只能回去打工赚钱,找人的工作也渐渐停了。
他们有过心理准备,二哥可能不会再回来了。父亲火化时,他们将二哥的一些物品一同烧了,和父亲葬在一起。但林再龙说,他们以为二哥是遇到了意外,是失足,没人想到他会成为一起故意杀人案的受害者。
他们自始至终没见过陈丰斌的家人,也没见过黄家人。开庭当天,林再龙和另外两个兄弟参加了庭审,通过视频看到了陈丰斌——那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年男人,方脸,中等身材。他的语气很轻松,林再龙说,“我在他脸上看不到一点愧疚。”说起当天的过程,陈丰斌的姿态也是随意的,“好像杀了一个傻子是没问题的,没有人会在意的。”
这让林再龙感到难以忍受。怎么会没有人在意呢?他的二哥不是判决书上宣读的林某,出生时,母亲陈香妹为他取名“少仁”,觉得念起来顺口,也好听。
小时候,父亲给几个孩子发零花钱,林少仁见自己没有,开口喊爸,问“为什么我没有”。那年林少仁9岁,第一次喊爸爸。陈香妹记得,那天丈夫高兴坏了,特地买回来一条大鱼,给家里加餐。
他们曾想为林少仁找一位妻子,以后能照顾他,但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也担心智障的基因会传给下一代,遂作罢。林家的经济不算宽裕,几个儿子打零工,租房生活。2015年,林家几个兄弟和父亲一起凑了20来万,建了套还算宽敞的平房。几个兄弟抽签,约定谁抽中了,房子就写谁的名,赡养父母和自家傻兄弟的主要责任也落在谁身上。
林再龙说,林少仁是家里最受宠的孩子,“因为他不懂事嘛,父母反而更疼他。”几个兄弟受父母影响,也已经有了默契,“如果父母不在了,那就由我们接着照顾他。”
在陈香妹看来,林少仁和其他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同。他经常看电视到深夜,她会骂他,“你还不睡觉,明天不用起来帮我扫地洗碗吗?”林少仁就嘟囔着,我知道,我知道。
因为常常自己出门,陈香妹说也不知道他跟谁学会了抽烟。但他知道拿烟给别人,要用两只手捧着递过去。有认识的人到家里做客,他会抢着泡茶,把茶碗端起来,恭敬地喊:“婶婶,来喝茶。”
林少仁小时候常跟着兄弟们到村子附近捡废品,捡来的塑料瓶就堆放在家门口的墙边,补贴家用,或者换烟抽。有一次他已经攒了五六袋废品了,结果全被偷了。他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没了没了,没有烟抽了。没有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但之后,林少仁再捡瓶子回来,不放门口了,会整齐地堆放在阁楼上。
“他很聪明的。”陈香妹喃喃重复。他会用父亲淘汰下来的旧手机拍照,用手机拍路边的鲜花和小草,还有大片大片的鱼塘。隔壁村子放露天电影是他最爱的活动之一,他带着手机过去,边看边拍,回来了就跟陈香妹展示各种并不讲究取景角度的照片。陈香妹夸他,你很棒,我都不会用手机。每当这时,他会露出一个有点骄傲的表情,“你差劲了,我少仁会。”
村口小超市的老板是他的朋友,不看电视也不看露天电影时,他出门转一圈,捡几个空瓶子,一屁股坐在小超市门前,呆呆地看别人打牌、跳广场舞。有人来买东西,有时他能听懂,就积极地帮超市老板递东西、搬大米。村里不喊他傻子的小孩也是他的朋友,捡废品攒了钱,除了买烟和零食,他还会买奥特曼的塑胶玩具,和游荡的孩子们一块玩耍。到了饭点,林少仁准时跟老板说再见,晃着两只手,慢悠悠地拖着步子回家。
除了那一天。一个从面包车下来的瘸腿男人,一把抢过他用来装废品的蛇皮袋,扔上车。林少仁探身过去想拿回废品,再没能回家。
他的骨灰最后被瘸腿男人扔进了百姓墓园门口的棚寮中,和其他无主尸骨一同下葬。
林少仁去世的这几年,陈香妹的身体越来越差,她做过几次手术,腹部一条长长的狰狞刀疤。她开始忘记一些事情,找不到儿子的照片,但又想找不到也好,“每次看到他的照片就会一直哭,痛苦。”她总会想到儿子失踪那天,她把楼上房间的灯打开了,她以前从来不开,“我想着他早晚是要回来的。”她说,“等他回来的时候看到那个灯,就不会很暗,不会害怕。”
(文中除林少仁、林再龙外,其余人物为化名)
原标题:《寻找尸体的人》
//@就叫熊太行也行 :和当年我们遇到的事情差不多。 2006年中国青年报发了一条《大学的钱该花在哪》,说中国人民大学中区食堂花了不少钱盖了个观光电梯。新闻稿上跟记者署名的有个实习生是新闻系的同学,校长纪某某括号副部级括号完暴怒,指示一查到底,发现我是这同学的班主任,实习是我推荐的,我就丢了教职……
 电影大概是没上映过我大脑自动补全的一部,我下晚课回来提着一碗大大的猪蹄,路过长的像扑棱蛾子的大飞机打开门,就看到应许的大家正在开火布菜,电视上投屏着电影片头,有点幸福
电影大概是没上映过我大脑自动补全的一部,我下晚课回来提着一碗大大的猪蹄,路过长的像扑棱蛾子的大飞机打开门,就看到应许的大家正在开火布菜,电视上投屏着电影片头,有点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