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完《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后,回头去读约翰·麦卡雷的原作小说,里面有很多冷战时期情报工作的细节: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谍报战并非是你死我活的搏斗,而是一群老干部看文件:从各种公开或非公开的资料中梳理出脉络,并得到需要的信息,最后的“脏活”往往只是情报到手之后的收尾,有时甚至是由临时找来的线人和编外人员执行,电影里那种特工全副武装在国外杀人越货的情形是极少出现的。枪战、暗杀、破坏之类的活动只是一小部分,更多是漫长枯燥的情报分析过程,这也是为什么CIA历史上的几个知名情报专家都出自耶鲁历史系,中国国安招人时也格外青睐历史专业,就是看中了他们对大量材料进行整理归纳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真有国安在监视你,更有可能是大腹便便的半秃中年男,而不是眼神锐利随时准备杀你灭口的特务……
#什么值得B
【声明】有可能是误伤,可能人家就是不太懂得网路礼仪,但是主页看下来真的很奇怪很想专门钓鱼的网警。我知道我关注数不少这样挂人可能会被认为是bully,但是世道不一样了大家还是小心为上。如果误伤我提前道歉。
【正文】今天被一个人关注点进去主页看感觉很奇怪。首先没有任何原创嘟,都是回复别人,而且回复也不好好回复,就会一直要微信。而且会乱at不认识的人要微信。关注了十多个号全都是比较常批评中国政府的账号。我觉得看着非常可疑很像是钓鱼网警就屏蔽掉了。大家可以看图自行判断。
(以及如果真的是钓鱼网警现在网警的智商和水平已经低到这种程度了吗?这能抓住谁呢?
附上🆔可以直接复制粘贴查看:[email protected]
给学生上课,记课时。一小时30分钟,记1.5h。
写下1.5h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小学一年级的我,写作业,题问一个半小时写成数字是多少,我答1.3h,因为一小时60分钟,半小时30分钟,怎么看都是0.3h,我还沾沾自喜,想着有很多同学肯定忘了一小时是60分钟吧。
姐姐帮我查作业,说是1.5h。我和姐姐挣了一个多小时,怎么也不能理解。
现在想想,就我的这个数学直觉,怎么后来能学理科?
现在想想,一年级的事情,我怎么还记得那么清楚。
总之,我小学还没毕业,姐姐就离开了。后来看望过我家一次。很多很多年没见了。
#大雉雄姿英发
梦到我和一些人被囚禁起来,看守我们的人是个变态,会随机挑人带去看守室性侵。有一天我起夜,被看守撞见了,看守把我带去看守室。
我一路上想着怎么办。
到了看守室,看守的小弟来了,看守出去了。小弟对我说,他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但他不能违抗看守。我说,那你偷偷录像吧,录监控,把看守的恶行录下来,等我出去曝光他、告死他。
看守回来了,听到我最后一句话是叫小弟拿相机,看守问拿相机干嘛。我装作斯德哥尔摩症娇妻,说好不容易和看守有独处的机会,想让小弟给我们合影。
看守被骗过了,看我很乖,他决定把我带去更“豪华”的场所。哗啦一下,看守室打开了一扇暗门,走进去,竟然是个大酒店,里面很多人。我观察着有没有人能救我。我发现这里的人打扮举止都像黑帮似的,而且都和看守打招呼,我想也许这里是黑社会,看守也是他们的一员。
大概酒店里没人能救我了,只有小弟坐在监控摄像的另一头。看守还沾沾自喜地向别人展示:这个囚犯是个傻的,自愿跟着我走!
然后就醒了,我以为接下来剧情该到我如何智斗反杀看守、与小弟合力暴杀黑帮,可惜智斗部分智不出来,只好醒了。
我看很多人在讨论抗争中女性的存在被抹杀的事情,我回家一路上都在想这个事情。在这样全民的抗争中,女性的存在和视角被抹杀似乎是很难避免的。尤其大陆人被关得久了,第一次站出来,很多人没有女权意识也很正常。我想来想去,该怎么在抗议中address这个事情,尤其是对来自各个阶层可能根本对女性女权没有任何接触的人,可能直接去讲女权主义理论和国家暴政是父权的终极形式很难得到共鸣,别人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还可能被嘲笑以及又被“先人权再女权”攻击。那么不妨试试下次带些铁链女、乌衣、彭帅相关的海报去。今年二月份全网沸腾,哪怕再不问世事的人可能都知道铁链女,再不关心女权的人可能这事也是一个trauma。从具体事件入手,告诉大家不要忘记暴政对女性格外的压迫,这跟不忘记清零对人的压迫一样重要。大家可以一起喊“释放乌衣!”“世界没有抛弃你!”“彭帅在哪里!”,可能要比去直接讲理论或者直接批判效果好一点。因为中共暴政不止一点,而哪怕自己不关心女权,我们反对的依旧是一个有压迫的社会体制,不关心女性的被压迫我们的目标始终无法实现。
然后就是希望女性朋友多去说这些,多在集会上发声这些,如果没有声音就永远不会有沟通和进步。
目前就想到这么多,如果有朋友还有其他好办法也欢迎在这条下面讨论。 
看象的动态,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
有一次,我在北京看演唱会,结束后和我妈大吵一架,我就决定那天晚上不回家了,但是又不想直接住酒店度过这一晚,就在附近吃了日料喝了酒,但是吃完喝完已经太晚了,我自己一个人又不敢去酒吧夜店,就坐公交溜达到了火车站附近。
下公交后,在那里我碰到了一个老大爷,我就问他这附近有什么住的地方吗,他问我是不是没地住,我说是,他说你跟我来,不用花钱的。我当时其实有犹豫,但是想了想这么大地方,怕啥呢,就去看看呗,可能也是酒壮怂人胆,我跟着就走了。没想到,他只是带我去买了纸质车票,打算去火车站里过一夜。
我一开始也有质疑,这进得去吗,我看大门都锁住了,没想到买了票真进去了,我就跟着他左绕右绕,来到了公共休息室。进去之后,我和老大爷坐在了最后几排,在一片昏暗中我往橱窗看,我看到了好多零散的生活用品,我疑惑的再仔细往前面的座位一探头,居然躺着好多人,他们都有被子枕头等生活用品。
我当时有些傻眼,我问老大爷,这些都是流浪汉吗,他看了我一眼,问我说你知道什么是上访吗。那年,《我不是潘金莲》在各大电影院上映,当时的我刚好看完这部电影,我点了点头,表示我在电影里看到过。老大爷接着说,这些大部分都是上访的人,没有钱住酒店,就住在这里,其实老有人来这里轰人,所以他们白天就会出去,晚上回来,车站快关门的时候,他们会躲在车站洗手间里,就等着关门了。有一次他们因为政治原因被彻底轰出车站,他们就跑到了公交车上住,或者车站外面的广场上住,又被来回的轰,直到他们偶尔故意松懈。总之,尽管如此努力,该见的人该见不到还是见不到,倒是轰他们的人总见到。
老大爷应该是北方某个村庄里的人,他的方言我实在是听不太懂,他还耳背,只是自顾自的说,再加上年头够久,我已经记不清更多细节了。我就记得当时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劲,怀着几乎确定的答案问他:“大爷,你怎么知道这些的啊。”老大爷说:“我曾经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接着我就想问到底为什么这么做,有没有结果,老大爷不知道是真的耳背,还是不愿意提起,笑着错开了话题。
后来,我和这位老大爷聊了一整晚有的没的。转天的火车是我的时间更早,我在打好招呼走到不远处后,最后又回头看了老大爷一眼。他佝偻着背,坐在那里摁着老年机。我想我永远不会再遇到他了,也可能我永远很难这么直面的看到这些了。
当年的我是真的没想到,疫情三年,比那晚我了解到的,还要荒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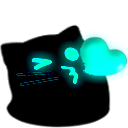 这是效果图,实物图的印花大小可能略有不同,过几天更新实物图,链接做好了会放上来!
这是效果图,实物图的印花大小可能略有不同,过几天更新实物图,链接做好了会放上来!

